《讀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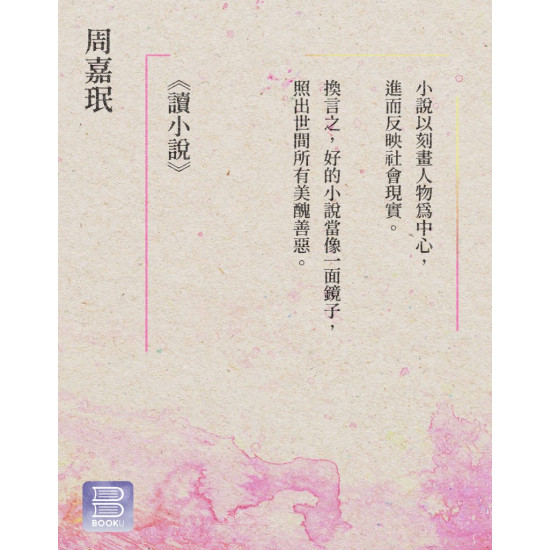
鍾曉陽為李維菁《人魚紀》撰寫的後記有一句話問:讀者用寶貴時間閱讀一本小說是為了什麼?小說和藝術所能給予人類的又是什麼?
我認真想了好久。
混跡閱讀群以來,我聽說過不少書友與閱讀的“緣起”。有的因閱讀改變了生活,有的因此成了更有靈魂的人,有的更說很為閱讀的自己感到自豪。聽著這些故事,我覺得驚奇的同時也不免一些羨慕,甚而有點疑心自己根本沒有自己想像中熱衷閱讀。蓋因我從不覺得自己與“閱讀”有什麼足以稱道的故事,閱讀就像是種生理需要——渴了想喝水,餓了想吃飯,困了想睡覺,實在乏善可陳。
我愛讀小說。正確點說,我是個愛聽故事的人。
相信很多人小時候都曾經愛讀故事書,只是長大以後見識了花花世界裡的火樹銀花就漸漸不愛了,而我在見識了花花世界裡的光怪陸離以後反而愈加妄想把童年的尾巴牢牢拽緊,不想丟失唯一的真,故而不曾戒去讀故事書這一嗜好。我曾因此而懷疑自己的閱讀能力,甚至妄自菲薄地以為小說就只是拿不出手的閒書。然當我認真地思考鍾曉陽所提出的問題時,我才發現自己讀小說並不單是為了調劑與消遣,更多的是小說家點破的那些大家都心知肚明卻又遮遮掩掩的人性。
分辨人性正正是我讀小說的最大樂趣。
曾見人指《人間失格》太喪,沒有半點正能量,大庭葉藏就只是個濫交的爛人;亦曾見人說《紅玫瑰與白玫瑰》只是個見異思遷的負情故事,佟振保就只是個大渣男。這樣的解讀並非不可,但人性絕非如此簡單。
各人有各人的價值觀,由各人的生長環境、教育、經歷、性格等形成,難言對錯。小說就像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縮影。讀的人自然可以打開上帝視角,站在道德最高點去評論小說人物的是非過失。但凡書中人物有半點不合乎理想的舉措,便全然否定整部作品,甚至作者。然平心而論,這現實生活中是否真有毫無底線的“好人”和徹頭徹尾的“壞人”?好與壞是否又真的可以單憑一個人在某一個時間點的某一個情境下的某一個抉擇而蓋棺定論?
在這個網絡語錄橫行的時代,小說遭人斷章取義早非新鮮事。譬如《圍城》“婚姻就像一座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裡面的人想出來”;而《紅玫瑰與白玫瑰》更被寫成了網絡歌曲《白月光與硃砂痣》,沒讀過小說,也沒打算讀小說的大約就因此而以為張愛玲寫的只是些少男少女的小情小愛。
其實,一部小說不單是作者的想像力和創作力,更多時候還是作者的思想與自我描繪。如此,了解一部小說的內涵就不只是熟讀文字那麼簡單,還得結合作者的創作背景、故事背景、人物背景、甚至人物的一句話和一個動作。這樣並非大費周章,純粹因為人心就是如此復雜。換到現實生活,誰會願意被人斷章取義,無理曲解?
如此細細琢磨,讀小說的同時也漸漸讀著自己,讀著生活周遭的人事物。
小說以刻畫人物為中心,進而反映社會現實。換言之,好的小說當像一面鏡子,照出世間所有美醜善惡。倘或讀的人因小說人物並非道德完人或併未過上理想生活而厭惡抨擊或加以鄙薄,那麼在回到現實生活的時候豈非要與世界為敵?我無意為大庭葉藏與佟振保辯白。他們的軟弱、自私與虛偽都有目共睹。但若結合的小說背景與人物的成長經歷來看,便能發現在這些令人厭棄與不齒的行為底下,他們不過和你我一樣,都是在時代巨輪裡找尋屬於自己位置的小人物。
說到底,喜歡與否終究是個人自由,閱讀更是個人隱私,根本輪不到旁人置喙。但若能在不喜歡的同時學會理解、包容與自省,並有所進益,那麼閱讀才算是真的閱讀。
特別喜歡《人魚紀》裡那句“從來就不是為了愛情而來,是為了困惑,為了靈魂,為了不朽。”
同樣,認真閱讀萬不應只是喜好,只是消遣,只是文青人設,還有困惑、靈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