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
16 J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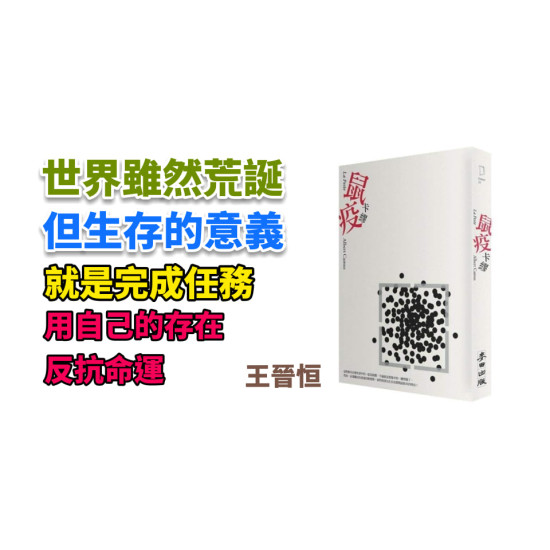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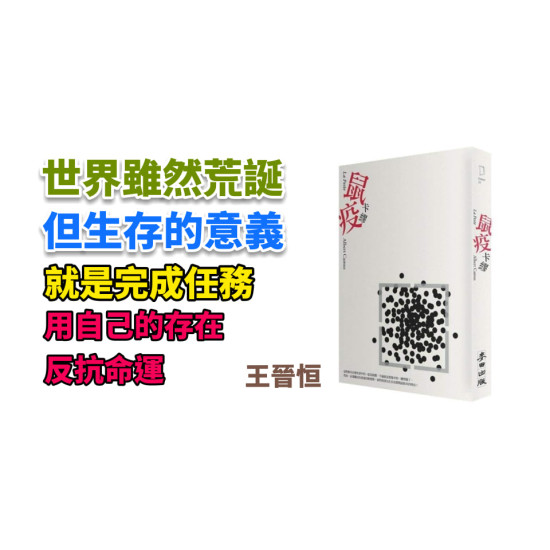
卡繆《鼠疫》
投稿者:王晉恆
《瘟疫,認命與反抗》
因為一場疫情,卡繆的力作《鼠疫》再次闖入世人的視野。有人對照書中的情節和當代人的防疫態度,意外發現了許多吻合之處。學者郭宏安曾把《鼠疫》定性為紮根現實的神話。所謂神話,和故事不同,它具有 “普遍性和超越性”,所以這部小說中的情節可以如此超前地刻畫我們當代人應對疫情的眾生相,其實一點也不出奇。
《鼠疫》是一本預言書?
卡繆不把這本書稱作“小說”,而曰“記事”,所以書中平鋪直敘地敘述這一場發生在北非法屬奧蘭城的鼠疫從突然爆發到莫名結束的整個過程,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疫情爆發前,省政府企圖抑制輿論,並為此次疫情是否該定義為 “鼠疫” 的字眼問題上糾結。人民普遍上十分樂觀,覺得古老的鼠疫不可能在他們的時代爆發,有些人則認為病情不會持續太久,當前的狀況都只是小問題。
然而當政府決定封城之後,人們陷入混亂,意識到事態嚴重。許多人來不及好好道別。人們因為聽信酒精可以殺菌的謠言而把酒館擠爆,有些人在報章上要求政府放寬一些封城的舉措,有些人甚至開始狂歡,試圖麻痺自己的恐懼。當疫情來到巔峰,棺材和葬地日益短缺,人們只好將屍體草草處理。普羅大眾失去個性和衝動,變得沮喪;而醫生們則漸漸木然和麻痺。多數人失去對宗教的信心,轉而迷信旁門左道。思念情人的人們則發現在他們失去愛人的肉體以後,由於封城太久,最後連可供他們追憶的影子也漸漸消失。所有城裡的人經歷了一種時間上的流放感,因為過去的記憶漸漸褪色,未來重獲自由的日子又遙不可及。上述種種,是否和當代許多國家或者自己身邊發生的情況弔詭地相似呢?然而,卡繆不是 “預言家”,他不過記錄了一段虛構的歷史,只是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浩劫當前,人應該聽天由命還是反抗到底?
大的敘事線重在寫實,而關於人類價值觀的衝突則由幾個故事角色在面對疫情時的談話中展開。奧蘭城有位神父,名叫帕納魯,他在佈道會上宣揚了他的“天譴論”,認為這次的疫情是人類該承受的懲罰,要人們在“死亡的陰影下去尋找賜予我們的恩惠”,聽其自然。這種 “積極的宿命論” 遭遇小說主人公里厄醫生的極力反對。他們都曾親眼目睹一位孩子因為鼠疫而痛苦掙扎然後慢慢死去,為此,里厄醫生無法苟同帕納魯神父的看法,因為無論好人還是壞人都有可能染上鼠疫,而孩子原本就是純潔無辜的,何來天譴之說?
“天主也許寧願人們不去相信他,寧可人們盡力與死亡做鬥爭,而不必雙眼望著聽不到天主聲音的青天。” 里厄如是說。
醫生和神父展現的,是在疾病面前兩種不同的態度——不作為和積極對抗。最後,帕納魯神父死於一種 “疑似鼠疫” 的怪病中,在在向我們證明了病菌的隨機性及殘忍,它不會因為我們的 “順其自然” 而讓步。
卡繆的 “鼠疫” 是超越疾病本身的。這部小說出版於二戰剛結束的 1947 年,令人不難將之和法西斯主義做聯想。奧蘭城裡對疾病初期不痛不癢的態度和當年歐洲人民在法西斯主義抬頭時的冷漠態度相似。其中一位角色塔魯是自願防疫隊的成員,因為曾經見證自己的父親判人死刑,而成為一位人道主義者。他無法接受這種以一個社會的名義褫奪人的性命的行為。所以從另外一個意義上,“鼠疫” 也是社會體制。
他說:“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鼠疫……每一個一舉一動都可能導致另一個人的死亡”。
我們都是 “帶菌者”,以間接或直接的方式判一個人死刑。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我們該如何自處,避免傷害他人?塔魯給的答案是 “意志”,努力不讓自己的 “病” 散播開來。這種立場可以狹隘地聯想到瘟疫時期人們所應該履行的隔離責任,但從更大的意義上來說,它代表了一種人類面對浩劫時所應該具有的積極和清醒。
另一邊廂,我們卻看到另外一些人走向“不作為” 的另一個極端——將個人自由擺在首要,並極力將之捍衛,就像某些當代人在染病後拒絕治療,甚至抗議政府通過封城剝奪人身自由。誠然,每個人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死。慢性疾病患者或癌症患者“拒絕治療” 的決定都值得被尊重,而傳染病則不然,因為傳染病患者在捍衛個體自由的同時,卻可能在不知覺間殺死一個人,剝奪另外一個人活著的權利。
小說的另外一個角色朗貝爾的故事,披露的正是類似的情況。他是來自外地的記者,因為封城而十分想念遠在法國的妻子,所以想方設法要逃出這座城市。曾參與西班牙內戰的他,決心不再為任何崇高的理念而戰,一心一意只想投奔到愛情的柔情當中。他認為奧蘭城應該將他放行,畢竟奧蘭城口中的公共的利益,也是由許多個體的幸福組成的,但這時他的幸福卻被箝制了。最後,當他發現里厄醫生也和他一樣無法與妻子見面,卻依然堅守崗位時,也終於放棄了潛逃的念頭,投身協助這一場異鄉的抗疫之戰。小說借著朗貝爾的故事讓我們明白了,人類在厄運面前,每個人都是命運共同體,哪怕像朗貝爾這樣的異鄉人也有一份抵抗的責任,沒有人是真正的局外人。只有大家做好本分,人類才有一線生機。
沒有英雄,只有責任。
卡繆不喜歡對英雄人物的歌功頌德,因為 “對高尚行為過於誇張,最後會變成對罪惡的間接而有力的歌頌”,這將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這個世界的善意是罕有的。然而這並非事實,因為 “人總是好的比壞的多……而最無可救藥的邪惡就是這樣的一種愚昧無知:自認為什麽都知道,於是乎就認為有權殺人”。里厄醫生反對英雄主義和聖人之道,他所感興趣的是做一個真正的人。他說:“這一切不是為了搞英雄主義,而是實事求是。這種想法可能令人發笑,但是同鼠疫作鬥爭的唯一辦法就是實事求是”。所謂的 “事實求是”,就是做好份內的工作。
如果要在書中樹立一個英雄人物,卡繆只推崇一位不起眼的人物,名叫格朗。他是一名老公務員,平平庸庸,閒暇時則嘗試書寫一部文學鉅作。疫情爆發時,他積極投入統計的工作,安守本分協助抗疫。卡繆將這種行為比喻成教師的教學工作——“他們只關心二加二是否等於四,而不管堅持知道這一個答案的後果是懲罰還是獎賞”。里厄醫生不喜歡來自外地的關懷套語和激勵句子,因為這種嬌柔造作 “不適用於例如格朗每日所奉獻的一份小小力量,也不能說明在鼠疫環境中格朗的表現”。
卡繆在描寫一座城因為一場疾病而被徹底改變的背後,實際上揭示了人類命運的虛無與荒謬。一場戰爭,疾病或天災可以將無數人從土地上抹去。既然人必有一死,那人為什麽活著?里厄醫生深明他投入的抗疫工作,無非一場又一場 “暫時的勝利” 和 “無數次的失敗”,但他為何還是堅持做下去?這不免讓人再度想起了反复把石頭推上山的西西弗斯。世界雖然荒誕,但生存的意義,就是完成責任,用自己的存在反抗命運。這是人類唯一的出路。反觀神父的 “天譴論” 所提倡的不作為,只會把人類推向更深的深淵。
歷史總是重覆。
最後,疫情在奧蘭城莫名其妙地緩和後消失。人們急著出關,慶祝著團圓;比較不幸的則在思念之情達到巔峰後印證了自己的親人已經離去的不祥預感。人們在一片歡騰的氣氛中慶祝鼠疫的過去。冷靜的里厄醫生卻樂不起來,他知道 “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衣服和傢具中歷時幾十年…….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
網絡上有人談起我們當前面對的是一場 “百年瘟疫”,因為每個世紀的第二十年,總會有一場奪走許多人命的疾病。雖然聽起來有些牽強附會,但可以肯定的是瘟疫總會在人類酣睡的時候再次從旁殺出,從來未曾離開。一場瘟疫,讓我們看到世上沒有哪一個人或國家是孤島。當下健壯的人不代表未來可以倖免於難,而已經宣佈成功壓制疫情的國家也不保證可以高枕無憂。
一切都會重來,就像黑格爾說過:“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當這場也許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疫情過去後,人們會重新過上正常的生活,漸漸遺忘所有教訓,重複著那些愚昧,忘記如何積極防備和反抗,然後繼續以為凡事都可以置身事外。按照這種規律來看,歷史會再次重演,無論我們面對的是百年瘟疫,還是隻手遮天的法西斯主義……
——————————————
投稿者:王晉恆
他說:醫學生,青年寫作者,曾獲全球青年文學獎和大專文學獎,作品散見於報章雜誌。
#BooKu
#讓書本找到對的人
#長期徵稿中
#直接PM小編就可以投稿啦
#不定時分享讀後感推薦好書
《鼠疫》訂購鏈接:
https://www.cite.com.my/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243927
